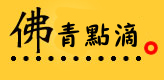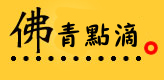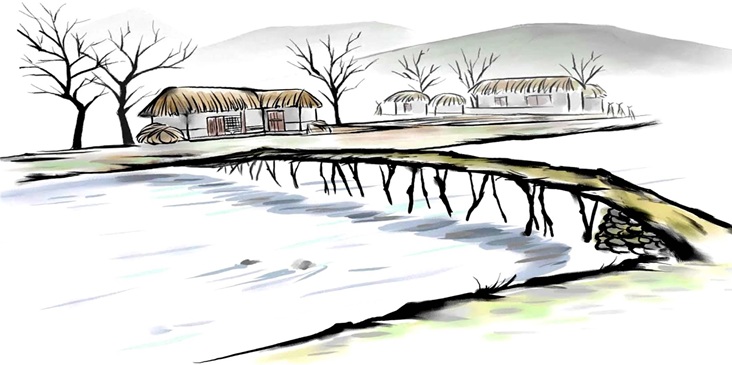
竟然又想起顏回,這位孔夫子的上首弟子。「賢哉,回也!一簞食一瓢飲,在陋巷,人不堪其憂,回不也不改其樂。賢哉,回也!」孔子這樣讚歎他的這位愛徒。最早讀到這段話在二十多年前,那時我還是一個少年,隻身在外求學。顏回的形象深深地印入我的心田,使我在寂寞中,心生一份莊嚴和自負。翻一翻《論語》,有關顏回的句子實在不多。其中主要是孔子對他的讚歎,除「賢哉」這一段外還有幾條: 其一,夫子說顏回終日聽他的教導,「不違如愚」,下去一省察,原來「回也不愚」。
其二,孔子問他的弟子子貢:「你和顏回比哪個強?」子貢忙答:「我哪能和顏回比呀!顏回聞一以知十,我只能聞一知二」,於是孔子感歎道:「弗如也,吾與汝弗如也!」
其三,魯哀公問孔子弟子中哪位好學,孔子說:「有顏回者好學,不遷怒,不貳過,不幸短命死矣。今也則亡,未聞好學者也。」
其四,孔子讚歎顏回「三月不違仁」,至於其他的弟子只能偶爾一至。
不過,這些記載中最能傳達顏回人格氣質的還是「賢哉」一段。這幾句話足以喚起我們對一位聖徒的想像:文弱,沉默;在偏僻的巷陌里,簞食瓢飲,兀坐終日;落落寡合,卻怡然自樂。
但不能說這是枯寂與逃避,因為這生命景象中透露出活潑與堅毅,那種以道自任的勇氣,確乎不拔的力量會使人發問:顏回看到、體悟到了甚麼,使他如此樂之不疲、隨順自安?
這不是我個人的想像。顏回確實打動了歷史上的許多人。最典型的是宋代以後,受禪宗的影響,儒者們捨棄訓詁辭章之學,轉而探尋孔門心法,他們關注的第一個題目便是所謂的「孔顏樂處」。
顏回身居陋巷,不改其樂,孔子是「飯疏食飲水,曲肱而枕之,樂亦在其中矣。」那麼,他們樂在何處呢?
宋代理學大儒周敦頤就教他的弟子程頤、程顥「尋孔顏樂處,所樂何事」,這分明就是禪宗參話頭的功夫。周敦頤曾隨佛印禪師參禪。
有一天,看見窗外草生,大悟,說:「與自家意思一般。」遂寫了一首偈語呈與佛印禪師,其中最後兩句說:「草深窗外松當道,盡日令人看不厭。」「看不厭」那就是其樂陶陶了。想必周敦頤體悟到了「孔顏樂處」。
顏回之樂,所樂何事?這對今天的我們是個難以參透的謎。顏回自然不是樂簞瓢陋巷,他不是一個以苦為樂的人,關鍵能雖苦尤樂。他的樂是自足自發的,不以外在環境為轉移,就像一股永不枯竭的泉水,汩汩不息,無有窮盡。朝如是,夕如是;貧賤如是,富貴如是;甚至,生如是,死亦如是。
慚愧呀,我們這些現代人!我們整日忙碌奔波,有幾個人能欣賞自性中那本有的安詳快樂?有幾個人能不借助外在聲色的刺激度過一個充實的週末?又有幾個人能獨自在燈下讀完一本聖賢書?很少很少。
所以,我們迷惘苦悶,會圍觀一位落水者的掙扎無動於衷,會無視街頭歹徒的暴行匆匆逃走;預言末日的流言蜚語會讓我們惶恐不安,巫婆神漢的魔幻表演能使我們心醉神迷......也有一些人冷靜下來,找到佛法。但我希望他們不要以急功近利和股票投機的心理去學佛,那樣會忘失自己生命中本有的財富而始終得不到安樂。
佛法是一種安樂法門,它是要我們以法自安安他,以法自樂樂他。這個法在哪裡呢?就在我們的自性裡,在我們生命的當下。如果我們能返觀內照,承擔得起,則樂自心生,向別人說一句都來不及。這,正是顏回之樂的真意。顏回,這位聖徒,他靜定的身影展示出生命本來的自然風光。我又想起他來……
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