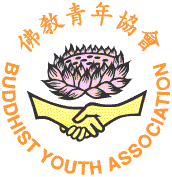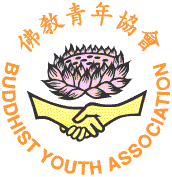|
支道林:即色本空 一代玄僧
支道林(三一四∼三六六年),本名支遁,名字行,俗姓關,陳留(今河南開封市東南)人。東晉時期的佛教學者。梁《高僧傳》卷目《晉剡沃州山支遁傳》
中稱支道林“幼有神理,聰明秀徹”。他出生在一個信仰佛教的家庭,從小便受到佛教文化的薰陶,表現出異於常人的見解,而他對於佛法教義更是有自己獨特的領悟。道林二十五歲時正式出家為僧,他先在吳建支山寺,後到剡〔今浙江嵊縣),晚年時候輾轉來到石城山建棲光寺。晉哀帝繼位後,詔令其到建康
(今江蘇南京〉,住東安寺,登壇講解《道行般若》,受到了社會名士和僧俗信眾的敬重,乃至朝野都十分悅服。三年後,他請求還東山,得到哀帝允許,
太和元年(三六六年)圓寂,世壽五十三歲。
支道林喜歡談論玄理,對《莊子•逍遙遊》進行了注釋,並有自己獨到的 見解。他在白馬寺與劉系之等人談到《莊子•逍遙游》時,有人說「各適性以為逍遙」,認為只要做到「適性」,就能達到逍遙自在的人生境界,而支道林卻不同意這種說法,他說:「夫桀、蹠以殘害為性,若適性以為得者,彼亦道遙矣。」夏朝的暴君夏桀以及大盜盜蹠都是以殘害他人為自己的性情愛好,假如他們也要隨順著自己的性情來,就能達到真正逍遙的標準,那麼他們也真算是逍遙了!
王羲之聽別人說起支道林對於《莊子•逍遙遊》篇頗有研究,最初並不相 信,後來支道林路過會稽,王羲之專程前去拜訪,向支道林問:「《逍遙》篇您可曾讀過嗎?
」支道林聽後,知道這是在試探自己,便作了近千言的一篇文 章,闡述自己對於《逍遙》一篇的見解。他的學識和才華,以及不同凡俗的見 理,都使王羲之由衷地信服,一連幾天都在討論《莊子》,甚至都捨不得他離
開會稽,生怕以後再沒機會一起探討《逍遙》篇了。
支道林在講解經書時有個特點,就是只標舉大義,但是對於詞句文章就不 免會有遺落的時候。那些拘受經文的人便以此事作為嘲諷他的把柄,說他沒有
學問,鄙陋無知,但是謝安卻十分欣賞支道林的這種講解方法,他說:「道林 講解佛法,就好比是九方皋相馬,九方皋在相馬時只要看出馬是否神情俊逸即
可,哪裡還需要管毛色是黃是黑呢? 」可見,當時的很多士人還是很欣賞道林 的,這與道林廣博的學識以及對於老莊經典的深刻理解自然不可分開,但是也
說明當時士人所推崇的是那種曠達灑脫、自然豪邁的風姿,無疑地,道林正符 合當時士人所推崇的標準。
歷史上流傳的很多故事,都足以說明當時高門士族對道林的尊崇。謝玄在 為親守喪時,道林前去找他,於是兩人就談起了老莊玄學上的一些問題,從早上一直說到傍晚,他從謝玄家回來後便對旁人說:「今天我算是與謝公暢聊了一回。」看來封建禮教也無法抵擋士人對於探討玄學的興味。
支道林之所以在老莊學問上如此下工夫,原因在於他主要是研究佛教般若學的,而般若學又與老莊的思想有近似及相通之處,因此,他經常用《老》
《莊》的道家思想來弘揚般若,這也是為了減少弘法時的阻力。而正是由於他 的學識、才情超出凡俗,也因為魏晉時代玄學思潮的發展,使得他與眾多社會
名流交遊甚廣,如當時的王洽、劉恢、許洵、郗超、孫綽、王敬仁、何次道、 王文度、謝長遐、袁彥伯、王羲之等,都曾與他往來探討學問。孫綽在《道賢
論》中,把道林和向秀相提並論,說:「支遁、向秀雅尚《莊》《老》,二子異 時,風好玄同矣。」而在《喻道論》中,他則說道:「支道林者,識清體順,
而不對於物。玄道沖濟,與情同任。此遠之所以歸宗,悠悠者所以未悟也。」郗超在寫給一位友人的書信中,稱讚支道林「神理所通,玄拔獨悟,實數百年來,紹明大法,令真理不絕,一人而已。」這樣的評價,可謂甚高。而在道林死後,東晉時期的畫家戴逵,從道林墓前經過,歎息道:「德音未遠,而拱木已繁,冀神理綿綿,不與氣運俱盡耳。」
晉哀帝即位之前就頗聞道林盛名,因此在即位之後便一連兩次派遣使者前去道林那裡,把他請到京城。道林走出深山寺院,來到了繁華的都市,住進了東安寺,主要講解《道行般若經》,道林在這之前就已經頗負盛名,而後又潛心研讀經書,修學佛法,如今更比以前講解得要深刻得多,因此道林此一番講解贏得了滿朝士人的嘆服。當時的一位名士王濛前來與道林談論,他事先構思好準備談論的內容,並用華麗的辭藻來做修飾,希望能駁倒道林。王濛口若懸河地說了好多,誰知道林卻並不對答,也不回應,王濛便以為支道林不是他的對手,因此越發得意起來,滔滔不絕地繼續說自己的觀點。道林聽完之後,只是淡淡地說:「我與你相別多年,今日聽您這些談論,您說話的技巧和水平果然進步不少。」當即王濛便現出羞愧的神情來,以後逢人便說:「支道林果然是僧人中的王弼、何晏啊。」
在東安寺的這幾年,道林日漸感覺不像以往那樣自在隨心,每天講經的時間很少,因為大部分時間都用在了及門宦士人的來往酬答上。也許道林感覺到在這樣的環境中迎來送往,是一種對生命的耗費吧,於是在進住東安寺三年之後,他便上書皇帝,懇請返回以前自己所居住的寺院。皇帝見道林執意要走,便不好多加挽留。道林要回東山的消息一經傳出,便引來社會名士紛紛前來相送,並贈送給道林許多貴重物品,其中有駿馬,也有珍稀的白鶴。當然,這些也引來一些人對道林的詬病,認為他一個出家人,居然還如此貪戀世間俗物。道林說他所喜歡的只是馬的風姿,白鶴的神情,而並非是它們所值的價錢。
根據梁《高僧傳》卷四所記載,支道林的著作主要有:《安般注》《四禪注》《即色游玄論》《聖不辯知論》《道行旨歸》《學道誡》《切悟章》等著作。在《即色游玄論》中,道林倡言「即色本空」思想,為魏晉時期般若學六大家之一。
支道林認為,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所眼見目睹的只不過是事物的表像(色),而並不是事物的本質(真如),因此,人們在認識上儘管有所感知,可是在客觀上卻並不一定確實存在這樣的事物。因為一切事物現象,都是待緣而後有,都要依賴其他的事物才能生起、存在、發展,自然也會消失、消亡。從這一層面上來說,一切事物自然都是空無自性的,雖然眼睛能夠看到它們,但它們不會永遠存在,因而也就不是真實存在的。
支道林是直接用佛教的緣起思想來說明般若空觀的,從這一點上來看,似乎是脫離了魏晉玄學的範疇。但是,從他的思維方式上分析,就可以看出其實他並沒有超出玄學思想體系中「本末」範圍,完全割斷了本質與現象之間的關系,而且支道林把色(外部事物)與真如(內在本質)完全對立起來,這也不符合般若學的中觀思想。
支道林作為東晉時期的著名高僧,他一方面與當時的官僚士大夫保持著廣泛而密切地交往,擴大了佛教對社會文化的影響力,他的才華以及人格情操都為當時的士人所傾慕,而且道林還創造性地用玄學語言來闡釋佛教的般若義理,創立了即色宗一派。
道林有一位相交頗深的同學名叫法虔,這人修行多年,也頗通玄理,與道林來往很密切。可是忽然一日,法虔就去世了,道林聽到這個消息後感歎道:「法虔去後,我便再無知音了。」之後便一病不起,在寫完《切悟章》之後,道林也圓寂了,這一年是太和元年。
—— 擷取自《高僧說什麼》─ 作者:馬超 ─ 出版商:中國財富出版
(待續)
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