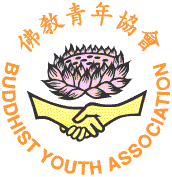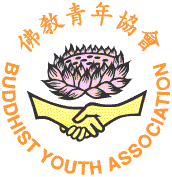|
那個禪者,是我多年的好友,得了不治之症,在禪坐中面對死亡,參悟死亡。作為好友,臨終前我經常去看他,聆聽他的教誨。我每去,他總在端坐,消瘦的臉上帶著微笑。我們坐下聊天,他說:「我一生被虛名所誤。雖然外面看著風光,出了書,有人跟著我學佛,可我知道,自己並沒有真正開悟,也沒有明心見性,現在想來,聰明反被聰明誤。」
他說得很誠懇。我說:「古來宗師,不是也有臨終開悟得道的麼?」他說:「那是大修行,放下萬緣,一靈炯炯,不是我這種聰慧的小根器,我一生太聰明,太有才,太有情,因此有太多的放不下。」我又問:「那你最近如何用功?我每次來,你都在禪坐,我不忍心打擾你,在外面念佛,為你祈禱。」
禪者淡然一笑,說:「謝謝。生死大事,何時死,乃至來生何處投胎,我還是知道的。」我說:「這就是大修行啊,你都知道你何時死,投胎何處,你還沒開悟?」禪者有點赧然,說:「這只是功夫,與開悟沒關係,更與明心見性沒關係。我出生到三歲,就能記憶投胎的因緣,長大後學佛來求證這因緣。我此生很早就知道自己『生從何來』,一生的修行只為完成『死向何去』,現在能知道死期,不過是預知時至而已,『死向何去』,我也知道了,不過還是那句老話:『再入輪回做眾生』,我的內心已經沒有對死亡的恐怖,這點粗淺修行離得道或開悟或見性還遠著呢。」
「那你最近如何用功?」
禪者說:「一心懺悔那些業障,從內心淨化。我是一個將死之人,要在臨死前,把內心清理干淨,這幾月我一直在懺悔。懺悔我造的業,懺悔我做過的錯事,懺悔自己沒能真正盡孝,懺悔自己曾經傷害過朋友、親人,懺悔曾經說了很多妄語,在修行上,未得言得,未正言證,自負輕狂;懺悔自己曾經口是心非,說了不少是非,惹了不少麻煩,給他人帶來了不少傷害;懺悔我對愛過我的女人帶來的心靈上的傷害;懺悔自己的無知對同修帶來的誤導……」禪者說了那麼多可懺悔的事情,說時還會流淚。他對我說:『一個人,在臨終前的大懺悔,就是「放下包袱,輕裝上路。」』說到這句,他笑了。誰都知道「上路」意味著什麼。
他要我找來一個農村人洗衣服用的大鐵盆,要我幫他把平生的文稿搬來,足足有一米高,要我當著他的面燒了。幫他燒?我不忍心,說:「這可是你一生的心血啊,多少出版社找你要書稿,為何要燒?不是很好嗎?」我不干。他說:「你不燒,那我自己燒。這些沒有價值的東西,不燒何用?我沒有得道,那些知解宗徒的文字,到頭來都是魔障,我自己是清楚的。燒了書稿,以免貽誤後學,以免增我罪過。沒有真正明心見性,所談所說盡是野狐禪啊,你想讓我墮落地獄嗎?」
他沉靜地說:「我一生說法講經,辯論是非,因為沒有得道,沒有見性,說了妄語和見地不正的話,報應在身,得病在口腔、食道、胃。」他的臉越來越消瘦,因為坐禪,精神尚好。
我和他一本一本地燒他的作品,包括他的日記,不少還是用毛筆寫的,字跡工整。大冬天,我們以書稿取暖。看著他的淡定與超然,我很感動,也想,我死前,要像他一樣,燒盡自己所有的日記、文稿,不留那些雜碎,干干淨淨,毫無牽掛地離開。我的念頭一動,他笑了,說:「別學我,學我沒出息。」
我來過多次,禪師都說在懺悔業障,懺悔過惡,他對我說:「口業最難懺悔,這一生中,我講經說法,口出妄語,說人是非,口業大如山岳。」他嘆口氣說,「盡管口業深重,我還是要懺悔清淨了再死。看來,我比預期的日子要晚死一月,這一個月專門懺悔口業。修道學佛的人,口頭禪也造業啊,何況我口業不淨,說是非,爭曲直,談邪見,不知這一個月能否懺悔清淨。等我懺悔清淨了,就是我要走的日子。」作為多年亦師亦友的人,我還是難過,問他:「你要走了,有什麼話作為對我最後的忠告?」
禪者說:「我知道你的未來之路,但不能說破,說破就是害你。未來的路在你心中,你如果能在夜裡靜坐內觀,也會知道的。我這一生的經驗,能告訴你的,就是:沒有得道、沒有開悟見性前決不為師,為師就害人,誤人子弟即誤人性命,果報嚴重,我的報應就在你眼前,所以,決不好為人師;
其二,你開悟見性,還要保任修行,修出更大的本領後再出來弘揚佛法,即便你有了弟子,記住,不要接受他人供養,決不剝削弟子,江湖上的事情我見多了,很多老師把弟子當僕人馬仔使喚,那個罪過很重;
其三,不要輕視任何不懂佛道的人,哪怕他們見解幼稚、錯謬,都不能笑人,我這一生笑了很多見解錯謬的人,結果自己遭到報應,每一個沒有開悟的人都是未來佛,一旦開悟就是大師,你怎能嘲笑大師?這道理我懂,但習氣、傲氣使然,給自己招了不少禍端,最近一月所懺悔的,就是我曾經輕視過他人;
其四,你以後去參訪他人,哪怕外道宗師,也不要帶著成見去參訪,不要比較誰高誰低,人間有無數菩薩化身教誨,外道中何嘗沒有菩薩教化?不要帶分別心和成見,你一心聆聽,內觀,內智自生,生而不住。我過去好辯論,好爭鬥,口誅筆伐,結果自己得了咽喉癌、食道癌,罪孽深重啊。」他說著眼淚流下來了,是懺悔的淚,是悟達的淚,也是教誨的淚。他用淚眼看我,「記住了?」我說,「記住了。」我這十餘年來也有一點點虛名,來拜師的人偶爾有,我深記禪者之戒,從來沒有收過「徒弟」。有人給我磕頭,我就趕快跪下給他磕頭。這都是禪者的教誨。
一個月後,他說:「我要走了,還是投生西北吧,西北窮一點,但人厚道,佛道的根源甚深,不像江南人,拿佛道賺錢,也不像東北人,骨子裡並不敬佛。我就投生西北,咱哥倆有緣,三十年後,還能再見,那時你是大哥,我是小弟,你可要幫我。」我們都笑了。我說:「我向你學禪時不上進,你踢過我,那時該我踢你囉。」他說:「踢狠點,爭取在你一踢之下,我當場開悟。」
他真的在認定的那天坐化,肉體火化。我分取了他一點骨灰,來京時還帶著,有一年,我發現窗外長的竟然是海棠,秋海棠,這才想起他的那首臨終詩:
海棠風過蟬魂香,寥廓青天是故鄉。
再來求道道安在?康寧福壽非吾望。
我恍然大悟,就把他的那點骨灰撒在窗外的海棠樹下。窗前原先有棵松樹,看了兩年,小區的物業把松樹移走,種了海棠,大概有五年了,夏天,海棠葉茂,無數鳴蟬在海棠葉下歌唱。海棠花紅的深秋,蟬聲已息,夜是那麼安寧,安寧得讓人猛然間不太習慣沒有「蟬嘈」的夜晚,「禪嘈林愈靜,鳥鳴山更幽」。蟬鳴聲不斷,顯出深林般的寂靜。我家住在一個叫「康寧居」的小區。《尚書》把「福、壽、康、寧、善終」當成人生的五福,那個禪者不求人間的五福,只求大道。
他最後一次顯露神異,預言了我未來的居處,他的骨灰會滲進海棠樹枝。他說這些都是無常的,離大道、離見性還很遠。就他這樣的修行還是沒有了脫生死,沒有開悟,沒有見性。寫這篇文章時,禪者已經坐化十多年了,想想自己的修為,慚愧啊。那個禪者是誰?我不願意說出他的名字,他把一生的文稿焚毀,不希望有人記住他。我相信,總有一天,我會在茫茫人海遇見他的,不論是否認出他,我們總會有緣遇見,盡未來際,會遇見他,在那個了無分別的本地風光裡會回遇見他。
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