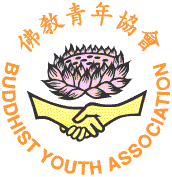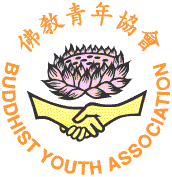印光大師。名聖量,別號『常慚愧僧』,陝西郃陽縣趙氏的子弟。出生才六個月,即患眼疾,幾乎失明。年幼時隨著兄長讀儒家的書籍,考取清朝科舉的秀才。曾經駁斥佛教,後來生病數年,才省悟以前的過失。二十一歲,前往終南山南五臺的蓮華洞寺,依止道純和尚出家。接著擔任湖北蓮華寺的知客,在曬經時得讀《龍舒淨土文》,知道念佛往生淨土的法門,才是了生脫死的要道,隨即專心念佛。次年受具足戒於陝西興安縣雙溪寺印海定律師的座下,因印光大師擅長書法,凡是戒期中所有的文件,全部都令他書寫。因過度疲勞而眼疾復發,於是感悟到色身為痛苦的根本,即於空閒時專念佛號,寫字時心不離佛,表晚大眾睡著後,又起來坐著念佛。等到事務完成眼疾也痊癒了,因此深信念佛的功德不可思議,後來印光大師自行化他,專一以淨土法門為依歸,就是由此開始的。
二十六歲時,聽到紅螺山的資福寺為專修淨土的道場,於是辭別師父前往參訪,入念佛堂念佛,淨土的行業大為進步。歷任上客堂(接待客人及內務)、香燈、寮元(掌理眾寮)等職事。以念佛為主要的修行,同時研究大乘經典,深入經藏,妙契佛心。三十歲,到北京的龍泉寺為行堂,三十三歲追隨化聞和尚將大藏經請回普陀山的法雨寺,之後住在藏經樓,閉門隱居精進修行。大眾請他講《阿彌陀經便蒙鈔》一部完畢後,立即閉關六年,又住在獨修的蓮蓬中,以期日夜念阿彌陀佛,儘早證得念佛三昧,而學行並進。
民國元年(西元一九一二年),高鶴年居士選取印光大師數篇的文章,刊載於上海佛學叢報中。徐蔚如居士先後以《印光大師文鈔》印行於北京、上海、揚州等地、,幾經增訂,流通的很廣泛,而受其感化者愈來愈多。因為有感於時值末法時期,世風日下,若不提倡因果報應,不足以挽救頹廢的風氣、端正人心。末法的眾生根機陋劣,若不實行信願念佛,則決定不能了脫生死而出離六道輪迴。因此凡是前來請益者,不論是貴賤賢愚,男女老幼,皆以敦厚倫常各盡本分,防止邪惡的念頭,心存誠信無妄的真心,諸惡莫作,眾善奉行,以及因果報應,生死輪迴等實事實理,諄諄不倦地啟發教導,令請益者深深地生起覺悟之心,以建立為人處世之根基。進而能夠以真正為了生死,發菩提心,信願念佛,求生西方之坦途要道,使之切實奉行,以作超凡入聖的捷徑。
印光大師雖然深入通達宗、教二門,卻從不談玄說妙,而使眾人皆能了知佛法然後親身實行,令聽者皆能受益,因此歸依的人非常多。依教奉行,而得以往生西方淨土者,也多得難以枚舉,更進而教化身陷牢獄的人。時常持大悲咒水、米,救度一切病苦危急之入。自奉儉約,待人寬厚,只要是信眾的供養金,全部代為廣種福田,捐助急難及賑災,救濟饑貧,為贊助各個慈幼院,教養貧窮人家的子弟。創辦弘化社,刊印贈送經書達五百萬部、佛像百餘萬幅;維護正法。中興淨土宗,其功德實在難以思議。
印光大師一向發願不作住持、不收徒眾,後來因僧俗二眾歸依的人很多,於是創建靈巖山的淨土宗道場,以便大眾共修。最後自己閉關於蘇州的報國寺,穿著破舊的僧服,平常吃粗糙的米食,依舊不改往常的本分,灑掃洗衣,一直到老都是親自去做的。每日的功課之餘,圓滿完成普陀、清涼、峨眉、九華等四大名山山志的修改編輯,以及《印光文鈔續編》的印行,恆順眾生,無有疲厭。
民國二十六年(西元一九三七年)冬天,為時局所逼迫,才移居靈巖山寺的關房。民國二十九年(西元一九四○年)十月二十七日略為示現些微的疾病,隔日召集大眾云:「靈巖山的住持不可長久地懸缺,就以妙真法師來擔任。」大眾表示贊同,於是選十一月初九日為升座的日期,印光大師說:「太遲了。」改選為初四日,也說:「遲了!」最後擇為初一,才點頭說:「可以!」接著對大眾開示有關本寺過去的發展和變革,長達兩小時,還共同商議各各事宜,自在安適一如往常,沒有任何生病的樣子。十一月初三日如廁後洗手禮佛,晚上仍然進用稀粥一小碗左右,告訴真達和尚說:「淨土法門別無奇特,但要懇切至誠,無不蒙佛接引,帶業往生。」
初四日凌晨一點半起來坐著說:「念佛見佛,決定生西!」說完後,即大聲念佛,兩點十五分取水洗手完畢,起立云:「蒙阿彌陀佛接引,吾去也。大家要念佛,要發願,要往生西方淨土。」說完後,隨即面向西方,端坐於椅子上,一心念佛。凌晨三點左右,妙真和尚來到,交代他要維持道場,弘揚淨土法門,不要學大派頭。然後不再言語,只是嘴唇振動念佛,早上五點,在大眾的念佛聲中,含笑安詳而往生,如入禪定,時年八十歲,僧臘六十年。
初五日午後三時入龕柩,仍舊端身正坐,面貌容色如生。往生百日後荼毗,得五彩色的舍利珠百餘顆,大小舍利花及血舍利千餘粒,牙齒全部存留下來,頭頂的骨頭裂成五瓣如蓮華的形狀。
(印光大師永思集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