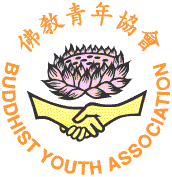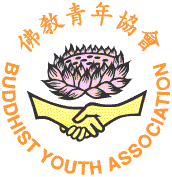昨天偶然逛書店,看到一位年輕人在看書,他吸引我的原因,是因為他捧著一本【楞伽經】來細閱。在香港,要找一個人看佛經原典已不容易,何況【楞伽經】義趣幽眇,文字簡古,讀起來詰屈聱牙;那不單需要一定的國學根底,還要有那份對玄奧學思的毓秀才質,更何況該讀者是一位年紀不過三十歲的人,然而他就予人一種靈根早種的意味。 昨天偶然逛書店,看到一位年輕人在看書,他吸引我的原因,是因為他捧著一本【楞伽經】來細閱。在香港,要找一個人看佛經原典已不容易,何況【楞伽經】義趣幽眇,文字簡古,讀起來詰屈聱牙;那不單需要一定的國學根底,還要有那份對玄奧學思的毓秀才質,更何況該讀者是一位年紀不過三十歲的人,然而他就予人一種靈根早種的意味。
年輕人看了看便挾在腋下,準備購買的樣子,跟著又拿起【解深蜜經】、【佛學總綱】、王恩洋的【唯識學】等。我趨上前問他是否佛教徒,他的答案亦正如我所料,他『不』是佛教徒。
有點調侃是不是?為甚麼我會有這種預感?因為我想起存在主義哲學家齊克果的一句名言︰『我不敢自居為基督徒,我只是想如何才能成為基督。』同樣地,佛教徒並不一定想怎樣成佛,想成就圓滿的生命;想成就圓滿生命的,不一定只有佛教徒,或佛教徒信奉的那唯一一套。
很明顯,這位年輕人是一位對佛法義理有深厚興趣的人,他很想從中找到圓滿的智慧,找到圓滿生命該走的路向,並成就之,否則他看的就不會是這類層次的讀物。
於是我和他閒聊起來,我先問他為甚麼不信基督教,他說因為不能忍受其霸道,以基督教獨尊唯一神而引起的排他性,雖不一定同意他以此理由而作出這抉擇,卻不難理解;但是問到為甚麼不皈依佛教,是不是不知道該皈依的道場,他說不是,他已去過許多佛教道場,就是因為去過,所以不打算成為佛教徒,原因?他的答案是︰『因為我覺得佛教很「俗」,跟我看佛經上的感覺全不是那回事。』若是身為佛教徒,很自然不會接受他的說話,但我卻不能不深深反思,為甚麼他對佛教有這種感受。
明明是一個拔苦濟厄,開迷轉悟,對一切存在本質有極深邃通徹的說明,從佛陀平等廣大覺性中流出清淨智慧,予溷濁世間一股甘露暖流的教派,為甚麼今天竟會被視為「俗」?是因為佛教為了媚嫵一般信眾,只會懸繒燒香,散花燃燈?還是為了配合及滿足「市場」的需求,對人生命本質的成長提升反而不加栽培,卻不斷提供人類情慾所需的東西,美其名曰「方便」、曰「先以欲勾牽,後令入佛智」,而使到佛教在有識者眼中變成這種異化了的產物?但如果要在這個地方投放資源,直接弘揚佛陀本懷的了義教法,會符合「市場」需求嗎?香港這個市場,是真的需要這種「產品」嗎?會對佛門中既得利益者有衝突嗎?
當時他有事在身,匆匆離去,未能詳加細問,不過我倒明白他的心情。
本人在弘法的過程中,也深深體會到,要一個教法生根並且茁壯,是需要適當的土壤,及適切的營養與水份灌溉,否則,這教法必然無法成長。
如果這地方的土壤、氣候、環境不能造就這顆種子,如果這地方不接受,或至少不重視顆種子成長後的植物會是甚麼樣子,這顆種子自然會另覓他途,找一個他該到的地方,一個需要他的地方,一個重視他價值的地方。
不同的土壤,形成不同的教派外觀;不同的氣候,使這個教派或盛或衰。我們只要看看哪種法門興旺,便知道該處地方人民的質素及取向如何。香港,會是甚麼的一種土壤?現在又是甚麼氣候?將來的氣流勢運又會往哪一方向走?
我們不妨翻開歷史,看看佛法由最初傳入中國起,這片土壤是如何吸收佛法,從菡萏花苗,到蒨蓊莊盛,最後草木零落,佛法被接受到冷落的原因,現在又似乎露出曙光的整個篳路藍縷的歷程。
佛法最初傳入中國,是為西漢哀帝元壽元年(公元前二年),據《三國志.魏書.東夷傳》所載,是博士弟子秦景憲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【浮屠經】(浮屠即佛陀另一音譯,有傳這部經為四十二章經),於是佛法便正式傳入中國,但當時的士大夫貴族,只當佛陀為另一個神祇來供奉祭祀。例如楚王劉英雖大力弘佈佛教,但其實他是錯誤地把佛當成老子一同祭祀(後漢書.楚王英傳),至後來的筰融,又只是基於政治上的考慮,藉免除徭役,收買人心,以圖發展軍事勢力,才大興佛事(參考《三國志.吳書.劉繇傳》)。他們都不是真的了解佛法,更遑論為佛法而作純正的傳播。何況漢武帝罷黜百家,獨尊儒學,到兩晉南北朝時代,魏太武帝亦曾經為了尊崇儒家政教及禮治,加上受道士寇謙之、崔浩的唆擺,於太平真君七年便下詔滅佛,開以後三武一宗滅佛之先河(參考《魏書.釋老志》)。以後佛法的弘傳,已不能不照顧到王臣貴冑的政治施策,及儒家、道家的思想影響。
雖然如此,卻還有不少人為佛法的高明而起仰止之情,晉武帝司馬炎曾大崇佛事,廣造伽藍;郗超崇敬支道林,說支法師神理所通,玄拔獨悟,數百年來只有他一人要以令真理不絕(參考《晉書.郗超傳》);石勒石虎之奉養佛圖澄,當佛圖登升展說法,即侍以下並助舉輿(見高僧傳.佛圖澄傳);鄉豪習彥威之極讚釋道安,說道安理懷簡衷,多所博涉,內外群書,略皆遍睹,陰陽算數,亦皆能通(在香港,即使有如道安這種博學的高僧,亦不易有習彥威這個伯樂),還有謝靈運、慧遠、范泰、竺道生、蕭子良等的弘揚,且兼有一定的佛學造詣及文化修養,佛教可說已漸趨興盛,至唐朝一代,大家都知道那是佛教的頂峰。
我們可以看看,佛教自兩晉南北朝時代已有一定規模,在貴冑及民間都有一定的認受性。據湯用彤佛教史稿所載,是因為這段時間佛教為適應當朝人民的需要,而自我調勻順化。湖南大學教授麻天祥先生更認為,佛教為了植入的需要,而趨炎附勢於黃老道術以求發展,所以佛道兩者的用字概念非常近似。例如道家言元氣,佛家亦言元氣;道家言樂施,佛家則有布施等(二十世紀中國佛學問題),所謂以『格義』的方式,將佛家義理由印度文字翻譯成中國文字。
當時的人民,或基於戰火頻仍,或基於世風敗壞,或基於外憂內患分崩離析的混亂情況,卻又無力扭轉,遂競相談玄,不大想理會國事政事。
然而,並不是說這時候的人民素質有所減弱,相反更是中國文化的一次倡極之風,與現在香港被形容為文化沙漠不可同日而語。
魏晉時所談論的「玄」,並非我們時下一般人所理解的只是高深。自十多年前某報紙以「不求高深,只求傳真」的宣示作招徠,切合一般香港人水平及市場要求後,好像要傳真就不能高深似的,更使大家競逐的,便主要為商業上的知識,以賺取金錢利潤,所以書局內教人創富的書最暢銷;或傾注心力留意娛樂圈醜聞,在歌星偶像中取得角色認同及共鳴、在明星的生榮死哀中取得感情宣洩;或政府的施政怎樣失誤,成為此製造有利於自己的政治本錢,或藉此招攬會員,宗教則招攬教友,以壯大規模及影響力。真的為民生生命提出有效解決方法,並付諸實踐的,真是鳳毛麟角。
如果你在坊間跟人談論的內容涉及宇宙或生命本源,而非他們生活(主要是物慾)所需,便會嗤之以鼻,正如老子所預見的「大笑之,不笑不足以為道」的現象。所謂「玄」,許慎的【說文解字】有如下闡述︰「玄,幽遠也。象幽,而人覆之也。黑而有赤色者為玄。」【太玄經】說︰「夫玄也者,天道也,地道也,人道也。」可以說,「玄」是包括一切存在之道理,當時談「玄」者的素質學養,如何晏王弼、嵇康張邈、向秀郭象等等,無一不是稟性鍾靈透脫,氣質俊逸之才(牟宗三先生亦於其所著的【才性與玄理】中讚他們多有高貴飄逸之氣p.50),而佛家深湛義理之能夠開展,與當時這些人也具高水平的素養學識有極大關係。
到隋唐年代,那不用多說了,從達摩祖師,鳩摩羅什祖師等來華,牽動了中國佛教的最高潮,吉藏、弘忍、慧能、玄奘、智顗、法藏、杜順、僧肇、窺基、荊溪、知禮、永明廷壽、臨濟義玄、百丈懷海、南嶽懷讓、圭峰宗密、法眼文益、溈仰、善無畏、一行大師︰︰等等等等,不勝枚舉。他們無一不是精英中的精英,無一不是韜藏深義、氣宇聳峻、靈辯滔滔、兼且文采斐然。
會昌滅佛後,迨宋明清數代,佛教越走下坡,直到民國,雖有太虛太師、歐陽竟無等提倡佛法,改革制度之弊。但中國與日本展開八年抗戰,之後的國共內戰,文化大革命等,中國整個文化土壤幾已到了乾癟衰枯的地步,佛教更是一蹶不振。
而香港又是甚麼時候才開始有佛法的流傳?這已不容易考證,印象中有文獻記載的,而且有系統地弘法者,早年有倓虛大師、羅時憲教授、根造上師等,近二三十年來,僧侶方面有聖一法師、暢懷法師、泉慧法師等;而居士方面則有霍韜晦先生、劉銳之上師、及談錫永先生一系列的甯瑪派叢書等,可惜他們不是已歸西方極樂,便是垂垂老矣,或移民海外。還在香港孜孜不息地弘揚佛法深義,而不是以灌頂加持,或財神供天諸禮懺法會為主的香港人,只剩霍韜晦先生等寥寥幾人而已。
萬德學會的常通師父曾經說過,佛教所以衰落,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人材凋零,這有兩種說法︰第一,是香港沒有這些人才,其素養不足荷擔;第二,是香港有這些人才,但佛教沒有足夠讓他生存甚至發揮的空間,於是這些人另行走他的路。從上文闡述的歷史可知,佛教興盛,有賴人才弘傳;現今在台灣,佛教人才鼎盛。在中國大陸,從所見出版的書籍看,與台灣不惶多讓。而日本,先不論思想內涵怎樣,但其對佛教文獻及歷史研究,確在世界佔一席位。
反觀香港,那種兼通八能、統攬三才的人,那種德行高妙,容止可法的人(參考劉邵,人物志)存在嗎?現在即使有這類才性的人,若沒有適當環境,也會淹沒於熙熙為利的滾滾紅塵之中。他們不是成為悲劇中的貧困分子,或大學象牙塔內顧影自憐的知識分子,便要把自己本性扭曲,參與爭名奪利的商業遊戲,鑽研於甚麼物流供應鏈管理,期權認股證買賣等科,或向「潮」(現今香港人對表達流行時尚的一個俚語)的路走。
雖然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,金融、旅遊、物流等行業俱為推動香港經濟的重要支柱。但這些只是外殼,只是硬件,香港最缺乏的其實是引導這些硬件往正確方向走的軟件︰︰思維方式及價值路向。香港人滿以為有獨立思考的能力,殊不知他們是被香港消費文化帶動,低俗膚淺的文化帶動,吃喝玩樂消弭生命的文化帶動,而沒有自己本乎生命向上的提升動力。林沛理先生更在『香港樂壇墮落的根源』一文中(亞洲週刊一月廿五日版),從梅艷芳的死亡,看到近年來的流行歌手走音懶音有之,歌詞不知所云,庸俗乏味者有之,但卻仍有無數的年輕人趨之若鶩,而評論當今香港年輕一輩已變成庸俗品味和偶像崇拜的奴隸,更可悲的是,他們遠為此沾沾自喜。
就算不想買櫝還珠,但能遊刃於名利場中又不失法度,雖和光同塵而仍能保心蓮綻放者有幾人?有多少現代的維摩詰居士?有多少像我在書店邂逅的那位年輕人?他的人生路向會是順遂還是坎坷?是為佛法注入新意象,還是湮沒於茫茫人海中?現今佛教,不要說培養出人才,能否保住人才也成疑問。
基督教培訓的傳道者大多有出路,至少不愁經濟拮据,佛教呢?
香港大學有舉辦佛學學士、碩士(將來可能有博士)等課程,但入讀需要有一定的學歷水平,即使六祖慧能亦未必符合其入學標準,學成後的出路亦未明晰可知(可能在有佛學課程的大專院校任教)。於是只好退而求其他,或讀志蓮淨苑舉辦的課程,或加入其他如法相學會、能仁書院,或各大專院校佛學班,例如珠海書院於一九七四年三月,由釋廣琳成立佛教同學會(是香港第一個在大專院校成立的佛學會)。
當然,除了辦學外,我亦不能抹煞其他弘法的方式,例如舉辦一些社區或青少年的活動,多做宣傳的工作,以現在青少年經常有反叛躁爆、動輒攻訐的行為,其實是非常需要正確的輔導。這些基督教都做得很有系統,甚至無遠弗屆(報紙專欄、電視電台、宣傳小報及單張等等,尤其那份宣傳小報【號角】,每月印製及派發量是十多萬份。相對於一份佛教小刊物【覺海清泉】的二千五百分,量方面如蚊蚋與鷲鳥之比)。
我曾參與不少基督教的團契,發覺來者都是因為生活上諸如感情、婚姻、人際關係、事業、財務經濟、病患、罪行等問題煩惱,在其他地方得不到關懷或援助,才參與這類活動,真為了尋求生命本源答案而來的少之又少。在那種地方,他們被關懷和尊重,並得以表達自己。有些團體更擺明是聚集一班為商務而來的生意人或專業人士,進入這類團體,在互惠下可得到無數商機。這說明了香港普羅大眾對宗教的要求及關切所在,而有關教派就為了滿足他們的需求,而供應這類產品。所以即使以往有美國【求真理】雜誌對聖經作出嚴厲批判,並找出一萬多點錯失矛盾;即使有尼采、費爾巴哈、羅素乃至聖嚴法師(基督教的研究)、印順法師(我的宗教觀)、何永坤(瞧﹗這個基督教)、李天命(思考藝術)、岑朗天(基督教的貧乏)等等多如牛毛的對基督教批判著作,雖然到現在還有基督徒無法回應以上著作的批評(因我在參與其團契時詢問過一些基督教朋友),但基督教並沒有因此衰竭,反而更加茁壯,更能通過自我反思而完善。這不得不說,基督教是對準了現今香港一般人的根器需要,而供給相應的教理或服務。何況許多並非出於聖經內容的其他宗教哲學家思潮,卻都納入為基督教神學或有關義理闡述,這些著作同樣是汗牛充棟。
佛教本身亦已為了自身發展,而供應一般眾生所需的產品或服務。然而我在上文中已說過,佛陀教法所以興盛,與人質素有莫大關係。因為他不是一個單單只是任人信仰求福的宗教;我個人認為,與其說佛法是讓人對生老病死苦的解脫,倒不如說,佛法是最終目的,是要讓一切生命按其本具之清淨本質,而自立自肯,而提升,而成長,甚至臻於至善圓滿,乃至不息地充周法界。所謂佛,本身就是一個圓滿的生命。這麼一種理念,不是沒成就的可能,諸佛菩薩,祖師尊者,都給我們起了示範作用。所以我覺得,現在香港最需要的佛教,除了是一個既可以令香港人「生活」質素提升(如為他們解決感情、婚姻、人際關係、事業、財務經濟、病患、罪行等問題煩惱),也可以令香港人「生命」質素成長的宗教(如先祖對法界性的體悟及闡述)。反過來說,要佛教不再流於庸俗,不再受人誤解鄙視,佛教徒(不論出家在家)本身的質素亦要提升,對國學,對佛法經典,對企劃組織管理,都至少要有一定程度的了解。
要成為佛法的阿闍黎(即教授師)或傳承者,至少要公開講述兩部或以上的大乘了義經典(例如華嚴經、圓覺經等),及著作至少兩部對佛法體會心得的書,並準備教育出至少一位接班人,因為這樣做才能使他真正面對諸佛菩薩的考核。而諸大菩薩護法若自己不想成為教授師,也盡力維護準備做教授師的人,使他不要活在三餐不繼、或負債累累的狀態下。否則,叫有能力的人如何肯為弘法出力?即使他不計較名利而仍肯付出時間精神,恐亦有心無力了。
固然,我並非要求每一位都有如宋理學家張橫渠那種「為天地立心、為生民立命、為往聖繼絕學、為萬世開太平」的氣概,但至少忠於自己的佛性,忠於自己的良知。由宋明開始,儒者講學至今,屢有新發明,義理的開拓上可說未有衰竭過,希望佛教徒也能從佛法上開出無盡的寶藏。
後記︰
曾經問過一位相識多年的朋友,我該如何弘揚佛法,希望他給予一點建議。他看罷一期我編輯的弘法刊物後,批評為垃圾可丟,因為這麼高深層次的撰寫方式,只會曲高和寡,以香港人現今的質素,根本不會看,亦看不懂。他建議我若想借佛法成名,就要來一舖狠狠的,抱著置之死地而後生,把佛門醜事搴出來,把佛教的種種缺點搴出來,把佛教來一個翻天覆地,因為香港人最喜歡看的就是這些。成了名之後,要弘法便容易許多,因為數千年來趨炎附勢的人性從未改變過。然而,當時我已斷然拒絕這種做法,一來無論佛教怎樣多醜事,已不需要我來搴,有些八卦週刊或報章已先行做了;二來,我不認為這對佛法的弘佈有正面幫助;三來,亦是最主要的,我過不了自己的良心。
梅艷芳一死,已有許多有關她的書刊承勢推出,有多少是真的為了紀念她?有多少只為了藉此賺取利益,然後期盼下一個明星的死亡?最近連『董建華的禍港陰謀』這類書也出了;看看在香港,以香港人身份出版有關佛法的書有多少?最近有一位葛雋先生出了幾本說禪的書,把禪理通俗化以應用於生活上,然而,他是一位基督徒。
或許因此我無法成名,無法得到某些利益,無法被一般人接受,甚至現在我的經濟已完全崩潰了,或許要面對死亡,亦當然知道沒有多少人會關心我的死亡;但我每次撰寫佛法文章時,我的對象不止是一般普羅大眾,而是在我面前,佛陀正在看著我,諸位菩薩祖師正在看著我,看著我表達是否如法,是否最好的法,我不是為其他人交代,我是向佛交代,向諸位菩薩祖師交代,我不能因為別人的水平而將佛法降低遷就,當然我會起用方便,但不可能永遠方便,相反,我想鼓勵他們,若要懂得如何欣賞佛法,懂得欣賞世間其他諸種更高層次的道理,與其要我們降低,甚至要我們不要表達,倒不如將自己的質素提升吧。懂得欣賞,才會讚歎,懂得欣賞,才肯尊重,懂得欣賞,才肯維護。
「六經責我開生面,七尺從天乞活埋。」這是明末清初的大儒王船山先生的銘言,其著作堪稱深邃艱澀,但為了學問能留傳,即使生死當前,亦沒有為了獻媚市場而稍作交易。
常人會笑他不識時務,但所謂「情必近於癡始真,才必兼乎趣始化」(張潮.幽夢影),若因此要我餓死,亦沒有遺憾。
(完)
|